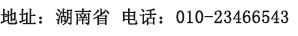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在这个日子,我要讲一个老作家,我喜欢的老作家,汪曾祺先生。
我常在故事里提他,写“续命”、“城隍”、“高邮水怪”时,都特别提过他。
这是一个温和、宽厚,充满人情味的老作家,他写四时食物,写旧人旧事,写故乡风俗,写鸟兽虫鱼,写草木四季,娓娓道来,温暖如画。
我读汪曾祺,已经有二十年了。
汪曾祺先生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如果说,每一个写文章的都有师承,那么我的师承,应该就是他。
第一次读他,还是初中,花了二元大钱,在旧书摊上买了一本《塔上随笔》。
这是一本很粗糙的书,排版设计都很粗糙,现在想想,也挺奇怪的,我为什么会买这么一本书?
我当时还是一个少年,心情总是很忧郁,每天都思考一些很玄很远的东西,有时候沿着水边走走,水边有上百亩桃花林,桃花开时,艳俗无比,我就不再出去,实在无聊,就躺在床上看书。
就看了这本书。
先看了《城隍》、《八仙》,看不懂,再看了《张大仙和毕加索》,《草木虫鱼鸟兽》,有点儿模模糊糊的意思了,说不上喜欢,却念念不忘。
等念了高中,又读了读,才觉得有些意思了,长见识,而且有人情味。
去书店找他的书,没有,又托了书店老板帮着找,终于找到了一本旧书,我记得上面还盖着一个图书馆的旧戳,这本书北京出版社出的《汪曾祺短篇小说选》。
终于读到了著名的《老鲁》、《受戒》、《岁寒三友》、《七里茶坊》这几篇名篇,读完后,已是黄昏,看着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突然有些恍惚,这世上竟还有这般美好的文字?
那一天,我感冒了,身体虚弱,躺在床上,一遍遍读着《七里茶坊》,黄昏下,黑暗一点一点淹没了这个世界,淹没了我,我闭上眼,在黑暗中细细品尝那种孤独之美,文字之美,难以言喻。
那时候我已经读高中了,我踢球很有天份,甚至一度被鲁能泰山青年队的球队球探看上,让我去济南试训。
我们高中,是一个很重视足球的高中,每次有外校来踢球,学校都要提前发公布,出通知,号召全校师生去给球员加油。
每次踢球时,都有几千人给我鼓掌呐喊,我走在大街上,满条街的人都站起来给我致敬,在路上经常能收到小女生的情书,现在想想,那真的是我人生中的高光时刻啊。
我那时候的梦想,是成为像罗纳尔多一样的男人,在风中拼命奔跑,让全世界的球场战栗、发抖。
嗯,以后让我们家千千千(三千,谢秦汉唐的小名)踢球,实现我的愿望。
但是那一天,我终于发现,原来文字也可以如此美好。
那么美好的文字,是否我有一天也能写出来呢?
我开始认真读书了,一边踢球,一边读书。
后来我念了大学,开始恋爱,开始失恋,文学就是这样寂寞,在你一路高歌时,在你站在聚光灯下时,你不会想起它,我忙着各种事情,谁有时间读书呢?
一直到我退学,开始四处漂泊,住在月租金30元的大杂院里,住在老满的仓库里,住在华山脚下5元一天的招待所,在每个孤独难捱的夜晚,我又开始读汪曾祺,读《草木春秋》,读《孤蒲深处》,读《晚饭花集》。
这世界上,孤独的人,并不只有我一个。
汪老先生是怎么度过的呢?
他写故乡的食物,咸鸭蛋,粽子,野菜,菖蒲,水鸭,蜻蜓,知了,写风土人情,写旧人旧事,让人读了感动,“这才是生活!”
这些温暖的故事,也支撑着我,一步步走过那些黑暗的岁月。
有一天晚上,我心情不好,喝了点儿酒,和生一宝宝细细讲起来我的童年,我的前半生,一桩桩旧事扑面而来,许多旧人旧事,再一次回到眼前,也挺有趣的。
她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她很后悔,没有早点儿和我在一起,这样就可以两个人一起吃苦了。
我就大笑,说我并没有过得那么糟糕吧?
再想想,自己那时候好像确实很苦,住三十元一个月的大杂院,屋子里只有一个煤球炉,我不会弄火,经常会熄灭,炉子一旦被熄灭,那是非常悲惨的,我需要用砖头砸碎大木块,用小木头渣生火。
当时我住在潮白河边,有一天,在河边捡到了一只很小的流浪猫,我就背着它,每天顺着潮白河干涸的河床散步,河床里全是沙子,有人在那里放风筝。
有一天晚上,异常寒冷,还下了雨,大木头上结满了厚厚的冰壳子,我砸了很久,也砸不开,只能哆嗦着上床,我只有大学宿舍里那床很薄的被子。
深夜,小猫冻得浑身发抖,我紧紧抱着它,第二天早晨,发现它已经被冻死了。
那是我第一次发现,我的虚弱,竟然连一只猫都保护不好。
我很难过。
后来和老满在一起,两个人摆地摊,当黑导游,还去新疆贩过玉石,活得像两只老鼠,破衣烂衫的,在三里屯大摇大摆走过去,想想也挺有趣的。
那时候的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成为一个作家,或者企业高管,或者任何一个人。
那时候,成天想着怎么搞点儿吃的,哪有功夫想这些啊!
现在想想,我和汪曾祺先生的经历也挺像的,都是幼时富贵,少年荒唐,青年努力,中年写作。
沈从文说,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
贾平凹说,汪曾祺是一只文狐修炼成老精。
其实,他这一生过得还是很苦的。
他的童年,是在无忧无虑中度过的。
他是扬州高邮人,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父亲是一个很好的人,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
他父亲很爱孩子,爱跟孩子玩,会很花很多功夫给孩子做风筝,用玻璃给金铃子做极精致的房屋楼阁,用浅绿透明的“鱼鳞纸”扎了一只纺织娘,用西洋红染色做重瓣荷花灯。
汪家有个很大的花园,有祖父建的几进的院子,院子里有小方厅、花厅,神堂、神龛、布灰布漆的大柱子,有龙爪槐、含羞草、荷花、绣球花、臭芝麻、紫苏,有螳螂、土蜂子、蝴蝶、云雀、蟋蟀。
几十年以后,他这样回忆童年生活:
有一年夏天,我已经像个大人了,天气郁闷,心上另外又有一点小事使我睡不着,半夜到园里去。一进门,我就停住了。我看见一个火星。咳嗽一声,招我前去,原来是我的父亲。他也正因为睡不着觉在园中徘徊。
他让我抽一支烟(我刚会抽烟),我搬了一张藤椅坐下,我们一直没有说话。
那一次,我感觉我跟父亲靠得近极了。
后来,他这样总结自己和父亲的关系:多年父子成兄弟。
他喜欢这种人情味的家庭,他们家也是这样,孩子叫他“老头子”,有点儿“没大没小”,是一个很有趣的家庭。
他后来考入了西南联大,在云南晃荡了几年,逃课,读书,写文章,去昆明大街上看匠人做东西,昆明多雨,青石板上总是湿漉漉的,空气中充满了菌子的味道,有车队走过去,叮叮当当的,都让他很感动。
四十年以后,他还记得昆明的雨:
昆明木香花很多。有的小河沿岸都是木香。但是这样大的木香却不多见。一棵木香,爬在架上,把院子遮得严严的。密匝匝的细碎的绿叶,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涨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四十年后,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
汪老先生老喜欢逃课,喜欢读杂书,后来英文和体育不及格,补考了一年,也没有考过去,索性肄业了。
这点也和我一样,我也是大学肄业。
肄业后,他先当了几年老师,在昆明,在上海,随便写了几篇小说,顺带结了婚。
后来就解放了,成立了北京文联,他终于混上了一份正经工作,在《北京文艺》当编辑,后来写了几个剧本,调到《民间文学》做编辑。
刚安稳了几年,他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
那段日子还是很辛苦的,起猪圈,刨冻粪,扛一百多斤重的粮食,他却自己给自己找乐子,画画(画马铃薯图谱),读书。
他的《七里茶坊》,这样描述这段生活:
我,就靠在被窝上读杜诗,杜诗读完,就压在枕头底下。这铺炕,炕沿的缝隙跑烟,把我的《杜工部诗》的一册的封面薰成了褐黄色,留下一个难忘的,美好的纪念。
有时,就有一句没一句,东拉西扯地瞎聊天。吃着柿饼子,喝着蒸锅水,抽着掺了榆树叶子的烟。这烟是农民用包袱包着私卖的,颜色是灰绿的,劲头很不足,抽烟的人叫它“半口烟”。榆树叶子点着了,发出一种焦糊的,然而分明地辨得出是榆树的气味。这种气味使我多少年后还难于忘却。
大冬天,写了很大的雪。
这样的大雪天,喜欢喝酒的,都要喝两口。
但是没有酒,怎么办呢?
那就海聊,聊酒,云南的市酒、玫瑰重升、开远的杂果酒、杨林肥酒,怀来的青梅煮酒……
还有美食!
昆明的美食,金钱片腿、牛干巴、锅贴乌鱼、过桥米线……
“一碗鸡汤,上面一层油,看起来连热气都没有,可是超过一百度。一盘子鸡片、腰片、肉片,都是生的。往鸡汤里一推,就熟了。”
昆明的菌子:牛肝菌、青头菌、鸡枞……
后来,江青一度很“欣赏”他,觉得他可以“控制使用”,让他参与写作了《沙家浜》。
作为八大样板戏之一,好多人应该都知道这部戏,不过大都不知道是他写的。
样板戏很刻板,每一句话都要审,他竭尽全力,还是尽量让它美好一些。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现在读读,还是很有气势的。
虽然,这个剧本让他吃尽了苦头。
再后来,文革结束了,汪老先生也平反了,终于可以写点儿自己喜欢的东西了。
这时候,距离他发表作品,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了。
大家纷纷评价:他是一个大器晚成的老作家。
其实,他少年时期就成名了,只是被耽误了而已。
那时候,他就写下了名篇《老鲁》,现在也是他的代表作,也是国内最好的文学作品之一。
不过他从不抱怨,只是安安静静写字,安安稳稳做人,他文章里从来都是一派和平,童年是有趣的,大学是有趣的,甚至连被打成右派,也是有趣的。
他自己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别人说,困难岁月都是逆来顺受,他却摇摇头,说人的一生,还是随遇而安得好。
这是一个很淡泊的人,他好像没有什么志向,或者愿望,脾气很好,总是小秘密的,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能有一间自己书房。
他工作几十年,后期写文章名动天下,却没有分到房子,全家老小挤在蒲黄榆那里一套很小的房子里(还是他夫人分的),窘迫不堪,甚至采访他的记者,只能和他去对面的花园拍照,不至于太寒碜。
他夫人的侄子施行先生,这样描述他的房子:
那是“文革”后北京最早建造的高层居民塔楼,厨房转不开身,厕所一米见方,没有澡间,没有厅,进门是一小过道,来了客人,他就在过道里沏茶。
一间7平米左右的小屋,比人家灶间还小,还挤放着一桌一椅一床,这就是汪曾祺的卧室兼书房了。白天,他把堆在桌上的东西统统搬到床上,写作。晚上再把堆在床上的东西统统再搬回桌上,睡觉。
后来,在妻儿的“威胁利诱”下,汪曾祺终于写下了此生一段最尴尬的文字:“我工作几十年,至今没有分到一寸房子……”
后来,他终于有了一间书房,是他儿子分配的房子。
他很高兴,终于住进了明亮的房子,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
这个名满天下的大作家啊,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夙愿。
虽然,他只在这里住了一年零三个月。
不过,这还不是最遗憾的。
汪老先生一生热爱家乡,他写了无数的家乡,最好的文章几乎都是在写家乡,他怀念着家乡风物,浩浩渺渺的高邮湖,旧人旧事,鸟兽虫鱼,他们家的老花园。
西堤外就是高邮湖,我们那里的人都叫它西湖,湖很大,一眼望不到边。湖通常是平静的,透明的。这样一片打水,浩浩渺渺(湖上常常没有一只船),让人觉得有些荒凉,有些寂寞,有些神秘。黄昏了。湖上的蓝天渐渐变成浅黄,橘黄,又渐渐变成紫色,很深很深的紫色。这种紫色使人深深感动,我闻到一阵阵炊烟的香味,那是停泊在御码头一带的船上正在烧饭。解放后,他家的祖宅被政府没收了,二百多间房子,只给汪家人留下了二间小小的,那是以前花匠住的。
汪老先生三次回乡,唯一希望的,是希望政府能将闲置的几间汪家旧宅归还,改善弟妹们的生活条件,自己以后回乡小住,生活起居和写作亦将比较便利。
他致函当时的女市长:“曾祺老矣,犹冀有机会回乡,写一点有关家乡的作品,希望能有一枝之栖。区区愿望,竟如此难偿乎?”
96年,这个女市长进京汇报工作时,主席特别说了一句话:“高邮还有个汪曾祺!”,一时被传为佳话,但也仅仅是佳话而已。
童年的旧梦,只能永远在梦里了。
汪老先生现在越来越火了,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个有趣的“老头子”,好多人慕名去高邮,想去看看汪老先生生活过的地方,就去那两间小房子,那里住着汪老先生妹夫金家渝先生,墙上挂着汪老先生的照片,还有老先生画的画。
好多年来,我一直想去高邮看看,甚至有一次,车都开到高邮了,后来还是决定回来。
都说近乡情怯,我却是近邮情怯,也许是怕伤害了少年时期的旧梦吧。
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平生很少求人。
但是我曾拜托过好多人,辗转联系到汪老先生的家人,希望可以高价收藏几幅汪老先生的画,作为纪念。
客观说,这些画,艺术成就并不太高,不过每次想起他的文章,总觉得他的画也是拙朴可爱,像那个老头儿一样可爱。
不过,汪老先生家人委婉拒绝了,说画不多了,还是放在家里吧,算是留个念想。
嗯,这才是一个“士大夫”家人说的话。
我也很骄傲。
那个,如果有人有汪老先生的画作,请联系我,我希望可以收藏。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好多人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那么我告诉大家吧。
今天,是汪老先生逝世22周年。
汪曾祺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有22年了。
我很怀念他。
我很想告诉他,二十多年前,那个很喜欢他的小少年,长大了,现在也成为了一个作家,也在试着和你一样,写一些寂寞而温暖的文字,希望能给这个孤独的世界,带去一丝希望。
我希望,能如你一般,诚诚恳恳待人,认认真真写字,做人和写文章,都干干净净。
我也希望,能如你一般,虽历经磨炼,依旧怀有一颗赤子之心。
我也希望,能如你一般,老了以后,还能成为一个有趣的小老头儿。
==
在小号
鱼叔怪谈,给大家推荐了一篇汪老先生的作品《双灯》。《双灯》原本是《聊斋》里的故事,汪老先生随手给“新编”了一下,改得极好,我读了无数遍,甚至让我也一度很想重写《聊斋》。
鱼叔讲故事长夜漫漫,鱼叔守护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