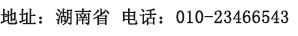时令一入夏,曲曲巷管家院子里的绣球花,热热闹闹地开放了。真的很好看,白、绿、红、紫、蓝,花朵又饱满又圆硕,仿佛无数的手举着绣球,随时准备抛掷出去。
管家的院门也是虚掩的,谁想来看,推开门就可进去。
院子很宽敞,栽种的几乎都是绣球花。高株和矮生的错杂为邻,品种有本地的“土著”:大雪球、大八仙花;也有来自日本的“远客”:恩齐安多姆、奥塔克萨。绣球花是易种易活的灌木,属忍冬科,繁衍后代主要靠“压条”,裁枝条而扦插,几个月后就花开如簇了。但它对土壤的酸性和碱性很敏感,比如大八仙花,花初开时是葱绿色,如果是酸性土壤,完全绽放时,花色就变成深蓝与浅蓝;若是碱性的土壤,花色则幻化出俏丽的粉红色。还有日本的那两个品种,花或先开如红霞继而变为湛蓝,或初放呈粉红再转化为粉蓝。只有大雪球,持守洁白与浅紫两种颜色,爱的是酸与碱中和的土壤。
来看花的街坊邻居,总要竖起大拇哥,说:“花开得这样好,管爷有好手段,也有好心境!”
管爷就是管锄畦,退休前是本地湘山公园的花木技师,瘦高个,窄长脸,脸上永远漂着憨憨的笑。他什么花都会侍弄,但最有体会和灵性的,是侍弄绣球花。湘山公园每个地段,他都熟悉其酸、碱度,碱性过重的,他用切碎的橘子皮泡水发酵后浇泼到土里;酸性太浓的土壤,用烧出的草木灰掺拌进去……在公园的游道旁、亭台畔、廓桥边,从夏至秋的几个月,成片成畦地开着各色的绣球花,引得游客纷纷买票前来观赏,如同洛阳城争看国色天香的牡丹。报纸上有个新闻标题最为读者传诵:“谁掷绣球光色影,满城争说管锄畦。”
管爷说:“过奖了,是我和同事们一起干的,怎么都算到我身上?将来退休了,我最想侍弄的还是绣球花。让想看的人看个够。”
果然如此。
这个夏天,绣球花开得特别喜气。
天天都来看花的是杨金,而且是华灯初上时,管爷和妻子袁瑛正在给花浇水。袁瑛原是湘山公园花木店的营业员,也退休了。
“管爷,袁婶,吃过晚饭了?我爹让我问你们好哩。”
“谢谢。你看中了哪一朵花,我们来给你剪下。”
管爷夫妇很喜欢杨金,模样文静,学问也不错,三十二岁就当上了环保研究所的副所长。杨家也住在曲曲巷。
“今天我想求一朵粉红色的绣球花。”
袁瑛说:“你应该是有女朋友了,好事呵。不能老当快乐的剩男,你爹妈都急得上火了哩。”
杨金的脸蓦地发烧,结结巴巴地说:“我……只是……一厢情愿……人家……还没点头。”
管爷说:“袁瑛,你话多了。快去剪一朵花来,别误了孩子的大事。”
“对、对、对!”
杨金拿着一支粉红色的绣球花,兴冲冲地走了。
管爷说:“你说杨金是剩男,我家那位在深圳工作的女儿,比杨金还大一岁,不也是剩女?”
袁瑛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我退休后栽了一院子绣球花,当然是我多年的爱好,其实也有我的祈愿:哪个小伙子能给女儿抛个绣球,或者女儿也给看中的人抛个绣球。”
“我……明白。”
有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才七点多钟,一个个子高挑的姑娘,推开管家的院门走了进来,然后又顺手把门带关了。
管爷刚给花浇完水,正坐在一个石鼓凳上歇息。
姑娘一直走到他面前,说:“你是管伯伯吧?我叫徐严,是个中学老师。我来看看你种的绣球花。”
“啊。欢迎。姑娘,你好像是第一次来这里。”
“可我听杨金多次说起你。”
管爷马上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说:“杨金是我看着长大的,好角色啊,对人有礼貌,工作又发狠,你的眼光不俗。”
姑娘浅浅一笑,问:“他一连送了我三十次绣球花,都是从你这里求的?”
“我的花原本就不卖钱,供大家看,也免费相赠。”
“那是管伯伯的雅怀。杨金求花一次两次说得过去,持久不断地求花,做人就有毛病了。花店里不是没有绣球花卖,他舍不得花钱;花是给大家看的,都像杨金这样求花,花只能屡遭杀伐,悲何以堪!”
“姑娘,杨金求几朵花,小事呀,不足挂齿。其实,你也不必这样苛求他。”
“小处见心性见格调。管伯伯,花是杨金求的,但我必须来表示谢意。再见!”
管爷还没回过神来,徐严的背影已闪出院门外,院门再轻轻带关。
在这一刻,管爷想起了女儿,只怕也是这样的人物。
太阳升高了,满院子金屑乱飞。各种颜色的绣球花,抹上了一层金黄的光影,在等待着脱手而出的机缘。
管爷的眼里忽然有了泪水。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