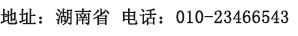曾经写过一篇关于盘扣的文章《柔情不断春似水,风情万种谁人弄》,对于盘扣的喜爱毫无抵抗力的我来说,还是忍不住再写一篇,细说那种由扣子带来的风情万种。
第一次穿有盘扣的衣服是姥姥做的小棉袄。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扣子是个稀奇的玩意,有钱也很难买到。于是,姥姥就学会了用布条盘各种各样的扣子。上小学以前常在姥姥家,每到冬天,嫌弃笨重的棉衣带来的束缚感,我总是游走在要风度不要温度的分叉路口上。手巧的姥姥为了让我穿上一件棉衣,想尽了一切办法,直到在我的一件侧襟开口的棉袄上缝了几颗盘扣,我才心甘情愿的穿上了花棉袄。
盘扣是那种特别简单的样式,姥姥先是把布裁成长长的布条,然后把布条的两边向中间对折,锁边缝住。再然后用筷子顶着一头,一点点的把有毛边的一面翻转过来,这就做成了盘扣时要用的布条。
而做盘扣的时候,也是我难得的安静时刻。围在姥姥身边,眼巴巴的瞅着那普通的布条在姥姥的手里变化着姿态,一会卷成圆筒,一会绕成绣球状。
经过姥姥的一卷一盘,盘扣的样子有的像蝴蝶,有的像一朵花,缝在衣服上,像蝶儿飞,像花儿开,穿上这样的衣服,心里别提有多美了。
都说三岁至小七岁到老,对于盘扣的喜爱一直未曾改变。
后来到了爱臭美打扮的年纪,就开始钟情于旧上海时代的画报。画报上那些美艳的女子,身着旗袍的妖娆自是风情万种。
而电影《花样年华》更是把我的盘扣情结植入骨髓。
电影中出现了23件旗袍,均由铜锣湾朗光时装的梁朗光师傅所制,设计师是张叔平,每一件旗袍都美得不可方物。不仅在外形上把张曼玉身材凸显的前凸后翘,风华正茂,妩媚风情;而且在气质上,张曼玉可以说是绝代风华,简直就像炎热的夏天里的一杯冻鸳鸯奶茶,喝上一杯真是能解所有身心之渴。
每一例盘扣都有表现其特征的名字,从普通直形扣到栩栩如生的蝴蝶扣、蜻蜓扣、菊花扣、梅花扣和象征吉祥如意的寿形扣等,有近百种之多。
那些端庄的小盘扣形状多变,有的像夏天原野上翩飞的蝴蝶;有的如古画上仕女怀抱的琵琶;有的活脱脱就是一芭蕉叶子,总有一种喜庆的的味道洋溢。即使是最简单的一字型盘扣,也可搭配高领或低开领的旗袍,演绎万种风情。
很难想象,没有盘扣的旗袍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一件旗袍,缺少了盘扣的点缀,这件旗袍无论穿在多么华贵的女子身上,注定要少去很多风采。正如张爱玲所说: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
始终以为,旗袍的美,不仅美在剪裁,更美在盘扣。
盘扣,不仅起到固定衣服前后襟的作用,还起到了装饰作用,让衣服看上去更加美观。旗袍与盘扣的完美结合,如高山遇流水。
盘扣的美,清新与淡雅相融,自然与人文结合,构成了一种服饰文化。将欲说还休的美瞬间表达出来。作为一种艺术品,盘扣堪称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朵奇葩。
盘扣虽小,却突显了中国人的讲究,包含了中华民族的独特的文化内涵。
盘扣是用于传统中国服饰上固定衣襟的纽扣,它在中国服饰的发展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盘扣不仅具有固定衣襟的功能,更是美的展示。小小盘扣蕴藏着质朴、自然的情愫,蕴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寄托和追求,还具有招福纳祥、传情达意的含义。
盘扣还是那个盘扣,但缀在不同款式的服装上却表达着不同的服饰语言。立领配盘扣,氤氲着张爱玲时代的含蓄和典雅;低领配盘扣、洋溢着90年代都市女性的浪漫和娇俏;短坎长裙中间密密地缀一排平行盘扣,于端丽之中见美感;斜襟短衫缀上几对似花非花的缠丝盘扣,于古雅之中见清纯。
盘扣有着浓郁的民俗气息,是中国服饰演变的缩影和中国服饰艺术的展现,也是中华民族经过长期的劳动实践与生活积累所形成的传统民间手工艺,更是机器永远无法替代的人工之巧。
盘扣锁左右,玲珑花瓣开,满满的中国风元素。
盘扣之美在于细节,或端庄、或优雅、或清新、或妩媚,盘扣的细节无一不向人阐释了中国美的真正内涵。
盘扣就如一把小锁,锁住了女子琼脂般的玉颈,典雅庄重,也锁住了女子心中深处的情绪,带着最娴静的东方韵致。
若非有丝丝情怀,何曾来同同心结。
柔情不断似春水,盘扣,像一阕旧词,又像一首婉约诗。一步一抹,款款而来,对襟流云,莲般的素淡,恰是东方柔情的再次盛放。
作者简介:
一片云:文字的堆砌者,语言的搬运工。时光可以慢慢苍老,时间却永远不会为谁停留,它是最好的写者。